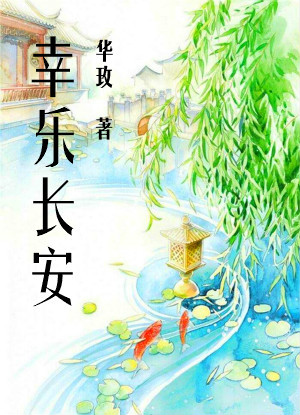
小說–幸樂長安–幸乐长安
漫畫–超麻煩–超麻烦
星耀學園
兩個月後, 金墉城,一間滿是潮腐之氣的小室裡。慕容麟躺在陳的榻上,悄無聲息地聽着窗外的喊聲。
窗外晚上深沉, 哭聲漸次。溼冷的雨氣, 順着閉合寬鬆的窗扇, 寂靜地溜進室內, 讓本已回潮的小室, 更添了某些陰涼。
世事難料,點子不假。慕容麟爭也沒思悟,不出五年, 他便又涉了一場摧枯拉朽,而炮製這場多事的人, 竟自他的五弟慕容超。
兄友弟恭, 在她倆慕容家, 完完全全是天真。
慕容超奪了他的權,奪了他的位, 還奪了他的……阿璧。
兩個月前,他統率兩千防化兵,兩千工程兵,脣齒相依一干朝臣,徊許州禳災。擺脫幹安城的第二天, 他吸收了一封來源於慕容超的信, 隨信而來的, 再有一隻微的烏漆函。
臨行前, 他下了道詔旨, 愛將國重任拜託給慕容超,讓慕容超在他趕赴許州禳災這段裡, 暫攝國事。他對慕容超素不撤防,由於這位五弟,窮年累月,煙消雲散作爲出分毫的詭計。
當年,在贛州興師,也是爲真的作嘔慕容德的金迷紙醉,大逆不道。惟獨,在深知團結一心也進軍後,他全速反叛了要好,尊從己的派遣,並尚無要和談得來一決高下。
收受信的下,他再有些迷離,是怎麼的事兒,能讓五弟在他背井離鄉僅一日後,就氣急敗壞地給他送信來。等到把信約看了結,他眨了下眼,臉蛋兒帶着點一葉障目的神情,恍如可以理解信中之意。
故此,他凝重着真容,低微頭,把信又看了一遍,這回看得省時,好幾一點地倒秋波,一番字一個字地看。看就這遍,他懂了,翻然懂了。
直觀賽睛,盯着信發了有會子呆,他把信居邊上,縮手取過隨信手拉手送給的小漆匣。漆匣一丁點兒,方正,其中放着不比崽子:一個一丁點兒的醬色錦袋,一隻芾的青釉五味瓶。
提起錦袋,抽開絆繩,他的手略略抖。絆繩全盤抽開,他探手進去,從內抽出了一縷頭髮。
毛髮黑糊糊柔滑,湊到鼻間,有點閉上了眼,鼻間有天南海北暗香傳,是了,是楊歡用字的沐發膏的意味,一股稀薄千日紅香。
除了頭髮,袋裡坊鑣還有小子,硬硬的,帶着點毛重,他重複探手進袋,這回,從袋裡掏出枚侷限來。他盯着手記,俄頃不動,一眼不眨。限定,虧得一天前,他親自戴在楊歡當下的那枚。
立刻,他對楊歡說,這戒指叫“併力戒”,像徵着他們的感情,他一枚,她一枚,戴上嗣後,至死不除,楊歡首肯了。而現在,他的那枚,還安慰地戴在他的小拇指上,另一枚,卻已躺在他的手掌。
微時而,墜髮絲,他提起了五味瓶,拔出子口的軟硬木後蓋,隨即,從瓶中倒出了兩粒藥丸。丸劑半大,棕黑色,每粒能有他小指甲蓋高低。藥是□□,吞食後,若無解藥,一度月後,服藥者渾身要害腫大,毛孔血崩而亡。
慕容超以楊歡的生相挾,逼他服用,逼他禪位。慕容超在信中說,他一經不想吃藥,不想禪位,想回幹安城懲罰他也行,有楊歡陪他聯手死,他不不滿。
慕容麟明白,慕容卓爾不羣給他寫這封信,那就說明,京畿內外,還是京畿外場的別的州縣,慕容超怕是也已做出對應佈署。數目人附逆,他渾然不知。但他亮堂,眼底下,諧調身邊但鄙人五千人耳。
就這般一聲不吭地寶貝兒把藥吃了,把禪位秉筆直書了,他不甘心。但是不吃,不寫,而慕容超真對楊歡行呢?雖說,整年累月,慕容超和楊歡的干係豎絕妙,但人心難測,他既能對他人肇,焉知決不會對楊歡搞?
慕容超給他節制了時日:一日以內,不能答問,楊歡生不保。
江山紅顏,孰輕孰重?
信,是午送到的,慕容麟漫天想了有會子,直至毛色完黑下。黯淡半,他命人點燈,取水,繼而,就着那杯不冷不熱的水,平穩地,把藥送下了肚。跟手,他又命人取來紙筆,一筆一劃,工工整整地寫入了禪位旨。
寫好誥後,他把它交付了送信之人。那人接了詔書後,卻並不急着走,然而跟他道了一聲“小臣得罪”,請他把兒縮回來,要給他號一下脈。
他一蹙眉,立即大白復,那人定是慕容超的潛在。藥也吃了,禪位旨意也寫了,他又怎會取決多號這一次脈。他伸出手,把子腕遞送信之人。
少年翻唱
那人也不功成不居,伸出三根指,按在他的寸關尺上。巡後頭,撤除指尖,對他稍爲一笑。慕容麟猜,那派對概是在驗,他是否果真服下□□。推求噲然後,脈像上,當是賦有行爲。
送信人拿着禪位詔走了。那人走後短,慕容麟“突發”急病,敕令立班師回京,不去禳災了。
五千師,經久不散地往回趕,到底在其次日巳時時節,慕容超界定的時期前,回來幹安。
漫漫“腐”一路
進了宮城,慕容麟沒去少林拳殿,而是直白回了嬪妃。去了也是白去。即或他在朝堂之上包藏了慕容超的言談舉止,又能何許?
慕容超是大毓,獨具燕國的至高王權,全燕國的兵都歸他管,都在他手心裡攥着。
王牌至尊
文臣光有嘴,消解兵,將倒是有兵,可那些兵也沒執政大人,精煉,還是頂消解。整宮城的中軍,揣測不是被慕容超齡買了,硬是已被他換上了友好的貼心人。開誠佈公隱瞞慕容超,非獨沒用,反是極有莫不,再搭上幾條生。
一進嬪妃,慕容麟就感到了好,在在都清幽的。雖,不怎麼樣宮裡也蠅頭熱鬧,但是這時的後宮,如約平常,更顯靜靜的。沉寂的宮巷,恬靜的宮院,冷靜的花木,肅靜的小樹,碩大無朋的後宮,靜得連一點諧聲也聽奔,靜得讓人深感遏抑。
他既沒去陸太妃的崇訓宮,也沒去楊歡的慶山水畫,可是直接回了上下一心的乾元宮。他在乾元宮靜謐地坐着,沉聲靜氣地等着,等着慕容超來見他。
熱情的 小說 幸乐长安 74.禪位 研究
2024年11月29日
未分类
No Comments
Francis, Hale
小說–幸樂長安–幸乐长安
漫畫–超麻煩–超麻烦
星耀學園
兩個月後, 金墉城,一間滿是潮腐之氣的小室裡。慕容麟躺在陳的榻上,悄無聲息地聽着窗外的喊聲。
窗外晚上深沉, 哭聲漸次。溼冷的雨氣, 順着閉合寬鬆的窗扇, 寂靜地溜進室內, 讓本已回潮的小室, 更添了某些陰涼。
世事難料,點子不假。慕容麟爭也沒思悟,不出五年, 他便又涉了一場摧枯拉朽,而炮製這場多事的人, 竟自他的五弟慕容超。
兄友弟恭, 在她倆慕容家, 完完全全是天真。
慕容超奪了他的權,奪了他的位, 還奪了他的……阿璧。
兩個月前,他統率兩千防化兵,兩千工程兵,脣齒相依一干朝臣,徊許州禳災。擺脫幹安城的第二天, 他吸收了一封來源於慕容超的信, 隨信而來的, 再有一隻微的烏漆函。
臨行前, 他下了道詔旨, 愛將國重任拜託給慕容超,讓慕容超在他趕赴許州禳災這段裡, 暫攝國事。他對慕容超素不撤防,由於這位五弟,窮年累月,煙消雲散作爲出分毫的詭計。
當年,在贛州興師,也是爲真的作嘔慕容德的金迷紙醉,大逆不道。惟獨,在深知團結一心也進軍後,他全速反叛了要好,尊從己的派遣,並尚無要和談得來一決高下。
收受信的下,他再有些迷離,是怎麼的事兒,能讓五弟在他背井離鄉僅一日後,就氣急敗壞地給他送信來。等到把信約看了結,他眨了下眼,臉蛋兒帶着點一葉障目的神情,恍如可以理解信中之意。
故此,他凝重着真容,低微頭,把信又看了一遍,這回看得省時,好幾一點地倒秋波,一番字一個字地看。看就這遍,他懂了,翻然懂了。
直觀賽睛,盯着信發了有會子呆,他把信居邊上,縮手取過隨信手拉手送給的小漆匣。漆匣一丁點兒,方正,其中放着不比崽子:一個一丁點兒的醬色錦袋,一隻芾的青釉五味瓶。
提起錦袋,抽開絆繩,他的手略略抖。絆繩全盤抽開,他探手進去,從內抽出了一縷頭髮。
毛髮黑糊糊柔滑,湊到鼻間,有點閉上了眼,鼻間有天南海北暗香傳,是了,是楊歡用字的沐發膏的意味,一股稀薄千日紅香。
除了頭髮,袋裡坊鑣還有小子,硬硬的,帶着點毛重,他重複探手進袋,這回,從袋裡掏出枚侷限來。他盯着手記,俄頃不動,一眼不眨。限定,虧得一天前,他親自戴在楊歡當下的那枚。
立刻,他對楊歡說,這戒指叫“併力戒”,像徵着他們的感情,他一枚,她一枚,戴上嗣後,至死不除,楊歡首肯了。而現在,他的那枚,還安慰地戴在他的小拇指上,另一枚,卻已躺在他的手掌。
微時而,墜髮絲,他提起了五味瓶,拔出子口的軟硬木後蓋,隨即,從瓶中倒出了兩粒藥丸。丸劑半大,棕黑色,每粒能有他小指甲蓋高低。藥是□□,吞食後,若無解藥,一度月後,服藥者渾身要害腫大,毛孔血崩而亡。
慕容超以楊歡的生相挾,逼他服用,逼他禪位。慕容超在信中說,他一經不想吃藥,不想禪位,想回幹安城懲罰他也行,有楊歡陪他聯手死,他不不滿。
慕容麟明白,慕容卓爾不羣給他寫這封信,那就說明,京畿內外,還是京畿外場的別的州縣,慕容超怕是也已做出對應佈署。數目人附逆,他渾然不知。但他亮堂,眼底下,諧調身邊但鄙人五千人耳。
就這般一聲不吭地寶貝兒把藥吃了,把禪位秉筆直書了,他不甘心。但是不吃,不寫,而慕容超真對楊歡行呢?雖說,整年累月,慕容超和楊歡的干係豎絕妙,但人心難測,他既能對他人肇,焉知決不會對楊歡搞?
慕容超給他節制了時日:一日以內,不能答問,楊歡生不保。
江山紅顏,孰輕孰重?
信,是午送到的,慕容麟漫天想了有會子,直至毛色完黑下。黯淡半,他命人點燈,取水,繼而,就着那杯不冷不熱的水,平穩地,把藥送下了肚。跟手,他又命人取來紙筆,一筆一劃,工工整整地寫入了禪位旨。
寫好誥後,他把它交付了送信之人。那人接了詔書後,卻並不急着走,然而跟他道了一聲“小臣得罪”,請他把兒縮回來,要給他號一下脈。
他一蹙眉,立即大白復,那人定是慕容超的潛在。藥也吃了,禪位旨意也寫了,他又怎會取決多號這一次脈。他伸出手,把子腕遞送信之人。
少年翻唱
那人也不功成不居,伸出三根指,按在他的寸關尺上。巡後頭,撤除指尖,對他稍爲一笑。慕容麟猜,那派對概是在驗,他是否果真服下□□。推求噲然後,脈像上,當是賦有行爲。
送信人拿着禪位詔走了。那人走後短,慕容麟“突發”急病,敕令立班師回京,不去禳災了。
五千師,經久不散地往回趕,到底在其次日巳時時節,慕容超界定的時期前,回來幹安。
漫漫“腐”一路
進了宮城,慕容麟沒去少林拳殿,而是直白回了嬪妃。去了也是白去。即或他在朝堂之上包藏了慕容超的言談舉止,又能何許?
慕容超是大毓,獨具燕國的至高王權,全燕國的兵都歸他管,都在他手心裡攥着。
王牌至尊
文臣光有嘴,消解兵,將倒是有兵,可那些兵也沒執政大人,精煉,還是頂消解。整宮城的中軍,揣測不是被慕容超齡買了,硬是已被他換上了友好的貼心人。開誠佈公隱瞞慕容超,非獨沒用,反是極有莫不,再搭上幾條生。
一進嬪妃,慕容麟就感到了好,在在都清幽的。雖,不怎麼樣宮裡也蠅頭熱鬧,但是這時的後宮,如約平常,更顯靜靜的。沉寂的宮巷,恬靜的宮院,冷靜的花木,肅靜的小樹,碩大無朋的後宮,靜得連一點諧聲也聽奔,靜得讓人深感遏抑。
他既沒去陸太妃的崇訓宮,也沒去楊歡的慶山水畫,可是直接回了上下一心的乾元宮。他在乾元宮靜謐地坐着,沉聲靜氣地等着,等着慕容超來見他。